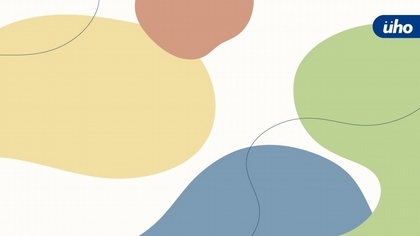(優活健康網記者謝劭廷/綜合報導)醫院總是給人一股肅穆的氣息,為打破刻板印象,一間位於嘉義的牙醫醫美聯合診所,在園區內展示了許多懷舊及具有地方特色之作品,如具有嘉義特色的石猴、木雕等,以及一台約百年的牙科診療椅。除了展示在地文化,這間診所還舉辦繪畫創作比賽,鼓勵幼兒園孩童到高中學生踴躍畫出自己心中的嘉義特色作品,請美術專業人士為參賽作品評分,並提供獎金獎品表示鼓勵。診所院長邱國杰表示,因為嘉義是人文歷史之重鎮,藉由充滿在地生活的藝術品展覽,希望激發出大朋友小朋友對繪畫的興趣及人文素養的培養,如此不僅能讓孩子們對自己的故鄉更熟悉,還能體會人親土親的精神。
#文化
「日本是何時獨立的?」我在國外的日本大使館工作時,每逢「國慶日」,就會有外國人問我這個問題。每個國家都有國慶日,按照慣例,駐外大使館都會在國慶日當天,舉辦盛大的宴會慶祝。有些國家是將獨立紀念日或革命紀念日訂為國慶日,有些國家則將國王的生日訂為國慶日,而日本的國慶日就是天皇的生日。由於日本國慶日當天,都會舉辦慶祝天皇生日的宴會,所以社交時的第一句必定是:「天皇陛下今年貴庚?」當然,這個答案非常簡單。接下來的談話就會延續此話題。過了一會兒,快要沒話題聊時,大概就會開始討論:「日本是什麼時候獨立的?」每當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時,都會嚇一跳。或許是因為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國家,都是脫離某國後獨立的,像美國就是脫離英國後才獨立建國,從這個角度來看,這個問題一點也不奇怪。然而,每次論及這個問題時,我總有一種特別的感慨。大多數的國家都是經由革命或獨立後才有現在的面貌,造成革命或獨立背後的民族苦難與民族自尊,多半就是形成「民族認同」的根源。日本曾歷經明治維新,也曾被同盟國軍隊最高統帥總司令部(General Headquarters, GHQ)占領,但日本人並不認為這些是革命或獨立。日本人對日本的感覺是「從以前就存在了」,畢竟日本並沒有何時、何地、和什麼人作戰以爭取自由的歷史。或許因為如此,日本的民族認同感也相對地較無法捉摸。這種「柔弱感」會使國人容易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、失去自我,可說是日本的弱點。當我與一位韓國的大學教授談論到這件事時,他說:「這不就是日本的優點嗎?」他認為,外表雖然柔弱,但內在具有不容動搖的堅定本質,所以不論表面如何改變,本質都不會變。或許正是因為日本外表柔弱,才能孕育出能夠順應變化的適應力,這也是日本的優點。太刻意強調某種文化,易產生排擠日本的民族性是「柔軟」,有些國家的民族性則是「強悍」。我在芬蘭進修教育學時,曾經陪同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們進行社會科校外教學,當時的地點是國立博物館。一到博物館,老師立刻帶領孩童們走到一幅畫前,上面畫著一位手拿書本的女性,以及一隻想要搶奪那本書的老鷹。老師對孩童們說:「這位女性代表芬蘭,她手上拿著的書代表法律。那隻又大又恐怖的老鷹就是俄羅斯,俄羅斯過去就像老鷹一般,奪取芬蘭的權利;這就是芬蘭的歷史。」芬蘭被俄羅斯統治一百多年,直到1917年才獨立成功。老師的用意或許是要教導孩童認識芬蘭過去苦難的歷史,但這種方式對小學二年級的學生來說,未免過於激烈。有些人認為,唯有具備民族一體感的國家,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生存下來。民族認同感越強烈的人,在國際社會中的表現也越活躍。也有人認為,既然現在是多元文化共存的時代,將多元文化發揮到極致,就有助於世界的發展。這種看法自有其道理,只是若行之過當,則有可能陷入國家主義或民族優越感的狹隘思維中。如此一來,非但多元文化無法並存,甚至會演變成攻擊或排擠不同文化的結果。1991年,位於芬蘭對岸的愛沙尼亞被蘇聯統治50多年後,終於重新獨立。愛沙尼亞宣布獨立的時候,廢除原本使用的俄語,改用愛沙尼亞語為官方語言。到目前為止,愛沙尼亞的改革都進行得很順利,但接下來的政策才是問題所在。政府宣布將針對留在國內、占全國人口大約三成的俄羅斯人,進行愛沙尼亞語的能力測驗,不及格者將剝奪其公民權。由於愛沙尼亞被蘇聯統治了五十年,國內已有不少土生土長的俄羅斯人,這些人既沒有回到俄羅斯的希望,也拿不到愛沙尼亞的公民身分,陷入極為悲慘的境遇,後來,取得公民權的條件才逐漸放寬。追求無謂的認同感,讓思想更狹隘也有些人認為在全球化的世界裡,並不需要國家或民族的認同感,每個人都應該從自己的價值觀中,發展出獨一無二的自我認同感。喜劇之王卓別林之所以於晚年時自稱「世界公民」,或許就是基於相同的理由。多元化的世界,是在人類超越國家與民族的藩籬後,由每個人共同創造的。近年來,因資訊密集化的關係,除了所處社會的價值觀外,孕育世界各地不同價值觀的資訊也不斷地影響著每一個人,形成個人的自我認同。然而,現實非常嚴峻,亦不如理想中美好,嚴格來講,想當「世界公民」,就必須拋棄家庭、拋棄故鄉、拋棄國家,只靠自己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。因此,任何人都當不了「世界公民」,這只是個理想。最近,日本的教育基準法和學習指導要領都做了修正,目的是加強傳統與文化的相關教育。教育的目的並非栽培「世界公民」,而是培育具有民族認同感的人才。(編按:台灣近來亦非常注重「鄉土教學」,重視地域性方言、文化學習。)然而,一味尋求國家與民族的認同感,只會陷入國家主義或民族優越感的狹隘思想中,失去原有社會文化的柔軟度,無助於國際社會中的和平與發展。因此,唯有連接不同文化價值觀的溝通技巧,重視對話,才能與多元化社會共存共榮。(本文作者/北川達夫)(摘自/1句話,立刻說服他/采實文化出版)
地址: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28號7樓之2
廣告合作:[email protected]
廣告合作:[email protected]
Copyright © www.uho.com.tw All Rights Reserved By 優活健康股份有限公司
Men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