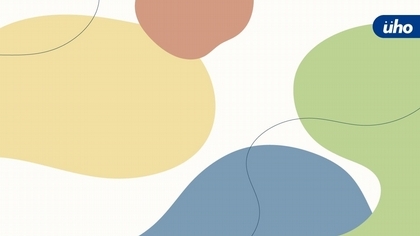坦白說,從前我是個想法極為負面的人,或者說個性極為悲觀。那麼我是怎麼改變成為如今這樣的呢?我想從「記憶」談起。我的父親是中學教師。在文教家庭中長大,得承受著必須成為「好孩子」的無形壓力。老師的孩子被問到想成為「好孩子」還是「壞小孩」時,只能夠回答「好孩子」。我既曾是模範生,也當過不良少年。小學四年級之前,我是眾人都拿我沒辦法的壞小孩。我曾在上學之前拿著鋸子出去,鋸倒附近鄰居的圍籬與樹木,事後母親只得臉色鐵青地挨家挨戶向鄰居道歉。上小學之後我變本加厲,常常激烈地反抗老師。我三年級的導師是個年輕的女老師,我經常惡整她,甚至把她給惹哭了,印象中這名老師只教了一年就離開了學校。升上四年級之後,換了一位男導師。他動不動就甩我耳光,令我過得非常不開心,那時我會推倒書桌、椅子反抗他。以現在的話來說,這或許就是校園暴力。老師曾被我惹得大為光火,將我趕出教室:「你滾出我的教室!」我還暗自竊喜,帶著一堆手下在校園裡玩。那天恰好下著雪,於是我要大家搓雪球,並且把石頭包在雪球裡,然後往教室裡扔。我們砸破了教室的窗戶,教室裡一陣騷動。總之,我那時總想反抗「當好孩子」的壓力,所以想盡辦法胡鬧。不過現在想想,當時我努力扮演著不符自身本質的壞孩子,那完全是抵抗不了壓力下的反撲。到了小學五年級,情況有了轉變。那時我的音樂老師問我:「你要不要來吹小喇叭?」結果我一吹就迷上了,從此之後逐漸變得積極,陸續擔任過學生會會長、參加正確騎自行車比賽得獎等等。我的行為與以前迥然不同,從壞學生變成好學生。但是當「好孩子」是很累人的事,我經常因而感到焦躁不安,久了偶爾還是會大暴走。就這樣度過不安定的青春期。小學畢業後,由於父親工作的關係,我們舉家搬到當時的西德居住。不過中學二年級時,我離開家人獨自回到日本,進入公立國中就讀。當時的導師教我如何以「日本男子漢」的姿態生活。這名老師學習武士道,背部直挺挺的,既威風又帥氣。這正是日本男兒的榜樣。我非常憧憬成為他那樣子,因此就讀高中時便加入弓道社,專心追尋日本人的精神。總之,我從「扮演好孩子」逐漸轉變為「演出理想的自己」。只是,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。若是仔細探討,我只不過是經常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,隨著別人對我的評價配合演出而已。進入東京大學後也是一樣。我最在意的仍是別人怎麼看我。就算是以司法考試為目標,內心的某個角落也會想著若通過司法考試,那真是太帥了。我以前就是這樣俗不可耐,總是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,扮演外人認為我應該是的樣子。(本文作者/伊藤真)(摘自/記憶的技術/商周出版)